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 王祖鵬攝影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 王祖鵬攝影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國際新導演競賽」自2005年起舉辦,是台北電影節除了「台北電影獎」之外的競賽單元,且是不分地區,放眼新銳導演的國際競賽。
「COVID-19」(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以下簡稱武漢肺炎)肆虐至今,各大產業停擺,影視產業也不例外。電影撤檔、延期,戲院院關門、歇業所帶來的票房損失自然不在話下,此外,世界各地的「影展」也因避免群聚紛紛停辦,壯如星光雲集的坎城影展也不得不鬆口停辦,影視產業幾乎全面停擺,但藝文工作者們仍舊試圖在艱困時刻突圍,或紀錄、或發現、或探問人類文明在疫情底下的眾生相。
疫情底下的影展應變之道,從實體轉往網路世界就是其一,由柏林、坎城、日舞、威尼斯、盧卡諾、翠貝卡、多倫多等全球21個影展共同策劃「We Are One」線上影展,讓影迷能在線上觀賞電影,是疫情世代下的另闢途徑,讓影像有不同方式的呼吸空間。
然而,「影展」還是人與人交流的地方,縱使「線上」能以更迅速、更效率的方式提供影迷觀影的管道,但仍舊無法取代當中的「人味」,「影人」、「影像」、「影迷」幾乎是構成影展的基本條件(當然還有廠商等等,族繁不及備載),影展舉辦與否牽涉的層面極為複雜,對產業影響甚大,坎城影展總監Thierry Frémaux就直言影展不能取消。今年邁向第22屆的「台北電影節」就是現今的例外,全台灣人民與政府相互配合,疫情未失控,成為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後,全世界第一個順利舉辦的實體大型影展。

做為台灣在年中的電影盛會,「台北電影節」(以下簡稱北影)除了觀摩影片單元之外,也設立競賽單元,分為兩種:「台北電影獎」及「國際新導演競賽」(今年則設有會外賽「台灣電影行銷獎」)。「台北電影獎」是專屬台灣電影的獎項,做為某種回顧、驗收台灣電影過去一年的成績,並展望未來,行之有年,也成了金馬獎之外影迷關注的焦點之一;「國際新導演競賽」則將目光望向國際,不限地域性地挖掘世界各地新銳導演的作品,此兩種競賽類型大相逕庭,卻同時透過北影存在,各具特色。
對比「台北電影獎」,「國際新導演競賽」對眾人而言相對陌生,為了更靠近所謂較為「冷門」、「生硬」的「國際新導演競賽」,特此專訪此單元的兩位選片人謝璇和蘇逸華,透過選片人的角度,理解「國際新導演競賽」的核心以及如何運作等諸多細節。
「國際新導演競賽」自2005年起舉辦,原名「國際青年導演競賽」,後來則發現某些新導演已非傳統年齡定義上的「青年」,創作者能否入圍也不應受到年齡限制,才更名為「國際新導演競賽」(以下簡稱國新)。也因此,舉凡是導演第一或第二部DCP / 35釐米長片,時間長度超越70分鐘且為台灣首映(台灣出品的電影便不在此限制中)的作品,皆具備角逐此單元獎項的資格,當然每一屆都有該年的時間規範,今年就必須為2019年4月2日後公開放映的作品。

獎項則分為四大項:「最佳影片」、「評審團特別獎」、「觀眾票選獎」和「台灣影評人協會推薦獎」。由專業電影人組成的評審團頒出「最佳影片」和「評審團特別獎」,評審團的組成當然也符合所謂的「國際」,歷來評審團成員包含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得主陳英雄、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得主魯本奧斯倫(Ruben Östlund)、日本名導濱口竜介(Hamaguchi Ryusuke)、山下敦弘(Yamashita Nobuhiro)、藏族名導萬瑪才旦、多倫多影展選片人喬凡娜芙維(Giovanna FULVI)等等,台灣代表也曾有資深剪接廖慶松、紀錄片名導沈可尚、知名製片李烈等等,今年則因疫情無法邀約國際影人,改由全台灣陣容領銜,由易智言擔任評審團主席,其餘評審包括導演蕭雅全、演員陸弈靜、監製陳寶旭和現任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執行長王君琦。
謝璇表示:「本來還是有嘗試邀約國際影人,大概去年12月左右就開始邀約工作,疫情爆發後,壓了5月1日前決定是否有外國影人來台,但其實在截止日前就覺得不可能成行。最後因應疫情,改為全台灣評審陣容。」
影迷們則能以投票的方式選出「觀眾票選獎」(每場電影映後都有觀眾票選單),最後則是去年新增設的會外獎「台灣影評人協會推薦獎」,由2018年成立的台灣影評人協會組成的評審團選出一部得獎電影。
「台灣影評人協會推薦獎」,類似「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補足影評的聲音,加上業界影人的評審團、影迷的觀眾票選,國新的獎項顧及「影人」、「影評」和「影迷」三種視角,讓競賽更加完整也具備多元性,甚至是片子本身也多一個被鼓勵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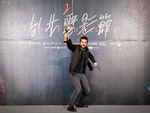
蘇逸華談起這次的合作:「當時是會長李光爵(膝關節)來和我們開會,希望能合作,雙方覺得國新不管是影像美學或創作形式都各具特色,希望透過影評人們用另一種觀點帶動片子討論。我覺得這樣很好,我們希望知道觀眾喜歡什麼,也希望藉由影評人的評論去了解選片人之外的想法,不管意見是好是壞,只要有增加討論度的東西都是好的。」
去年「台灣影評人協會推薦獎」頒給來自德國的《蘿莉破壞王》,最終評審團選出的最佳影片恰巧也是《蘿莉破壞王》,兩者不謀而合,至於評審團特別獎是韓國的《我們與愛的距離》,也特別提及了泰國的《邊境幻夢》,觀眾的心頭好則選出了台灣的《大餓》。綜觀這四部作品,風格截然不同。

《蘿莉破壞王》放眼在孩童身上,視覺風格強烈,同時側寫出社會照護體制上的無力與失能,並進一步反思孩童教育的問題所在;《我們與愛的距離》帶著點台灣新電影的氣味,誠懇地描寫女孩的私密成長,同時譜出家庭與大時代底下的隱約風暴;《邊境幻夢》如詩如畫,隱晦指涉受難的「羅興亞人」,在恍惚中帶出受難者的野性影像風格,更神來一筆使用鬼蝠魟的符碼意象;《大餓》在社會歧視、偏見的壓迫環境中,掌握住人類面對身體自主權的聲音。去年在影展見到這四部作品時,眼睛確實皆為之一亮。
離開北影,這幾部片子在之後的影展獎項成績也有目共睹,以最佳影片《蘿莉破壞王》為例,去年代表德國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前身為最佳外語片),又在今年有德國奧斯卡之稱的蘿拉獎中橫掃最佳影片、導演、劇本、女主角等8項大獎,事後來看,證明北影的獨具慧眼。

其實國新的確也挖掘出近年在國際引領風騷的影人,如今年以《兔嘲男孩》拿下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的紐西蘭導演塔伊加維迪提(Taika Waititi),2007年就以首部劇情長片《鯊魚愛老鷹》入選過國新(2010年再度以《BOY》參賽),同年來自挪威的尤沃金提爾(Joachim Trier)也以處女作《愛重奏》角逐競賽,後來尤沃金提爾以《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迅速成名,並數度入選坎城影展。
再來,以《出走巴黎》拿下去年柏林影展最高榮譽金熊獎的以色列導演那達夫拉匹(Nadav Lapid),在2015年以《吾愛吾詩》抱走國新的最佳影片,「看到這些人持續努力創作很開心,也很開心北影跟這些作者有了連結,或許有機會再把他們邀回來,辦個大師座談或焦點影人的放映。」謝璇如此說道。

說到底,國新的宗旨是要追尋新穎的電影語言、發現全新的可能性,創新、獨特甚至是顛覆性等等皆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而這世上也不乏鼓勵新銳的獎項,諸如坎城設有「金攝影機」獎、亞洲電影促進聯盟的奈派克獎等等;當然更有影展直接定位成鼓勵新銳,如美國的日舞影展、中國的西寧FIRST等等。
甚至在大型影展的主競賽單元也有此特徵,1994年的坎城看見了昆汀塔倫提諾(Quentin Tarantino)的第三部劇情長片《黑色追緝令》,勇於頒給昆汀金棕櫚;同年的威尼斯則找到蔡明亮的《愛情萬歲》和米丘曼契夫斯基(Milcho MANCHEVSKI)的《暴雨將至》,果斷將金獅獎頒給這兩位初出茅廬的新秀,金馬也在近年將最佳影片頒給張大磊的《八月》、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等新銳。當全世界影壇不斷找尋下一個大師,每一年給出的品味、眼光都不具相同,國新選片人又是如何看待自身的定位,甚至是創造出影展的獨特性?

蘇逸華說:「國新算是台灣唯一將國內外新導演做成競賽的平台,金馬關注在華語電影市場,且金馬偏向介紹大師級的作品居多。新導演不具知名度,在媒體獲得的關注較少,我們希望藉由競賽平台把這些作者和作品推出去,我們當然也看好他們的發展,而他們跟台灣的連結就是北影,之後如果他們有更卓越的成就,回過頭看,是我們發掘他們的。從選片狀況來說,在創作形式上,我們希望導演有原創性且敘事流暢,結構可能不一定完整,畢竟是新導演。」
謝璇則補充:「金馬跟奈派克的合作,只限於亞洲區的新導演,但北影的國新沒有地域限制,延續逸華所說,世界各地在自己的國家有鼓勵新銳的影展的重要性,大家常常講『立足當地,放眼國際』,當台灣有資源且盡可能將資源回饋給創作者時,我們讓這些創作者有平台更鄭重地去介紹他們初試啼聲的作品。再來是引進國際上不一樣的創作風格,於影展期間雙向交流,我覺得這是北影可以做到的事。而我們在找新導演的時候,常常在討論、說服、辯證的過程中發現大家都在找獨特的東西,為了這工作要看好幾百部電影,就能發現什麼是常見的、原創的,找尋新導演是變動的過程,在滾動中發現想要找的東西,我們只是在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影像風格,沒有一定標準。」
謝璇進一步說:「今年因為肺炎無法邀請國際影人來台灣,但往年這些主創團隊聚在一起時都是很開心的,這可能是觀眾看不到的,但看著創作者們交流與打鬧,我覺得這是影展很珍貴的地方。對我來說這是建立影展credit之餘,更讓我感到非常切身的。」

逐步做出口碑的國新,歷年來的報名作品件數不斷成長,以北影作為世界或是亞洲首映的新導演片子越來越多,去年件數突破600大關,成長至610件,今年則因為疫情影響,下降至412部,但仍舊照慣例從中挑出12部作為競賽作品。
這12部作品分別為來自日本的《阿伊努之森》、中國的《她房間裡的雲》、巴西的《流離公路》、科索沃的《誰是外來者》、葡萄牙的《鳥是海與樹的孩子》、秘魯的《無名之歌》、沙烏地阿拉伯的《人魚祭》、賴索托的《這不是一場葬禮》、丹麥的《我的好叔光》、烏拉圭的《夢遊潛水艇》,以及兩部台灣的《破處》和《惡之畫》,當中有兩部世界首映、四部亞洲首映以及六部台灣首映。
蘇逸華對選片徵件狀況做說明:「我們有選片小組,謝璇和我之外,還有會外三名人士,除了片子自行投件,我們也會主動詢問國際片商或製作公司,邀約符合資格的試看帶,類似邀請制,邀請的片子和自行投件兩個部分加起來,就是目前412部的徵件狀況。」
謝璇則補充:「由於我們工作上是很積極在挖掘國際新導演的作品,在邀請的部分就比投件比例還要高一點,但從數字觀察,自行投件的比例不斷增加,國新的知名度也越來越高。」
412部的報名作品,選片小組共五人要去消化、吸收,蘇逸華表示希望會外的三人小組每人看到50部以上,每一部都會有筆記、評論,而謝璇和蘇逸華則是從去年跑影展到今年徵件截止日4月1日前就看過無數電影,彼此看到喜歡的作品,就會先丟出來討論。
蘇逸華解釋:「在看片及邀片的過程,除非我們覺得某部片很可能被其他影展搶先邀走,有這個層面的擔心我們才會搶先把競賽邀請遞出,否則我們小組還是希望充分討論後才把遞出競賽邀請,所以就算我們先看過這部片子,還是會多等一些時間,多一點討論。當然,除非是我們認為很熱門的片子。」
由於北影在每年6月底舉辦,6月之前的影展,有柏林、日舞、翠貝卡、鹿特丹、盧卡諾等等,許多想闖蕩歐美影展的片子都會選擇這些大型影展作為首映地點,這些影展也成了北影選片的養分之一。
這屆國新入圍者,包括日舞影展奪下評審團特別獎的《這不是一場葬禮》;翠貝卡影展斬獲評審團特別獎的《阿伊努之森》;鹿特丹影展最佳影片金虎獎《她房間裡的雲》;柏林影展新設立的「邂逅」單元拿下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的《鳥是海與樹的孩子》等等,細看這一屆片單,會發現某些作品已經在國際舞台上發光,這樣的「得獎」光環,是否會影響選片人的眼光?帶著先入為主的成見或壓力看待片子?
謝璇和蘇逸華一致表示盡量把片子的標籤或得獎光環撕掉,單純以觀眾的角度看作品帶來的感受,謝璇說:「壓力其實在得獎片子上,片子先在大影展獲獎,大家在看之前可能會有某種期待,或許無意識會用更高標準去嚴格檢視。有了光環,往後就要背負更大壓力。但說真的,每個影展的評審團組成都不同,標準也不一樣,還是回到我們自己身上,怎麼去欣賞這些作品比較重要。」

蘇逸華說:「在鹿特丹影展看過《她房間裡的雲》後驚為天人,在今年中國獨立製作上這部片子很突出,所以在鹿特丹映後就動念把這部片子邀來,其他幾部就等小組討論後才決定。而這些片子在其他國際影展受到肯定難以避免,我們不去想片子們在世界上產生了哪些化學變化,希望純粹看片子長成什麼模樣及導演的創作動機等等。」
謝璇補充:「過程中當然有些片子的狀況是:不管最終進到觀摩單元還是競賽單元,我們都希望能在北影做首映,這樣的片子我們就會先發出邀請,發出邀請的意思是我們會請對方把首映條件給北影,之後經過討論,若想放進競賽單元再來和劇組談。例如今年入圍國新的國片《惡之畫》就類似這樣,去年底看過完成的影片覺得很好,馬上就問劇組能否在北影做首映,至於之後進入國新才是大家討論的結果。換句話說,我們先把《惡之畫》拉來北影做世界首映,之後才放到國新中。」
而這12部作品中,選片小組會希望至少有一至兩部的台灣電影,也希望都看過所有符合資格、能角逐國新的台灣電影,再做最終片單的決定。其實觀察每一年的國新,會發現地區性的廣度其實是夠的,以這屆為例便涵蓋11個地區,片單盡可能不被侷限。至於今年入選國新的兩部台灣片《破處》與《惡之畫》,都受到兩位選片人的高度欣賞,共識很高,入選就無懸念。
《破處》為《九降風》副導林立書的第二部劇情長片,故事描述在兩名將成年的少年「神器」與「阿烈」,兩人突發奇想,要幫助「神器」在成年夜買春「破處」,卻意外弄出人命,進而開始「棄屍」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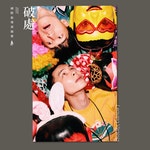
從《九降風》的基礎上來看,《破處》再度描寫青春時期的荒鬧生活,新世代的創作手法全部入戲,手機直播的媒材轉換也運用得宜,同時善用插畫凸顯風格,展現年輕生命對「性」的渴求與試探。片子前半段充斥旺盛生命力。但從屍體開始,影片做出巧妙轉折,在「棄屍」公路之旅中,對友情與生命提出辯證,「破處」二字便有了厚度且抹上一層晦暗,不再是單純的幻想,而是現實的重擊,片子後半段提煉出青春期的迷惘與徬徨。就成果而言,林立書的確另闢台灣電影類型的另一種可能,雖然結尾稍嫌倉促,但對於新導演來說仍舊完成度極高,或許在今年會成為票房和口碑上的黑馬。
對於《破處》,謝璇坦言最初不抱期待:「原以為是笑鬧喜劇商業片,但《破處》的結構其實很穩,它是成長故事、公路電影,魔幻且寫實,導演貫徹到底,很有生氣,不管是不是台灣出品,一個新導演剛起步,要在預算內成功執行電影的多層面向,能做到我覺得非常佩服。」
蘇逸華則說:「原本也以為《破處》就是單純的青春YA片(Young Adult,泛指校園喜劇類型片),沒想到核心主旨很沈重,甚至聯想到《猜火車》,當然這部片還是很娛樂,但真的不僅是嘻笑打鬧。」
至於《惡之畫》則是曾入選金馬電影學院陳永錤的首部劇情長片,題材碰觸了隨機殺人犯,透過極富才華的受刑人討論藝術與罪行的面貌,謝璇說:「《惡之畫》是社會寫實的,且有獨特美學,我們都很愛這份精緻的美學,作為一個新導演陳永錤影像掌控能力很好,且跟台灣土地的連結性很強,故事完整,角色也磨的不錯,以一個新導演來說很值得被介紹。」
對於《惡之畫》蘇逸華也補充:「覺得有台灣導演願意用處女作討論這個題目很大膽也值得鼓勵,當然也處理得很好,影像構圖與眾不同,跟台灣其他新導演相比有自己的氣息存在。」
對於台灣的新片,兩位選片人都覺得今年是大年,有《破處》和《惡之畫》兩部風格、題材截然不同的作品,在同一單元競賽,不管結果如何,都賦予台灣作品新的朝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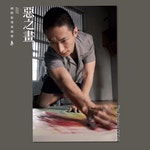
其實除了國新之外,北影的觀摩片有名為「未來之光」的單元,今年「未來之光」共有10部片子,包含去年在坎城影展影評人週展映的《春江水暖》;日舞影展全球劇情片類評審團劇本獎的《下落》;平遙電影節臥虎單元羅塞里尼榮譽最佳影片的《熱病幻夢》等等,一部一部展開來看,也是新銳導演齊聚,或許讀者會感到困惑,「未來之光」作品是否「不夠好」,進不了競賽單元?
不過細看這些作品,也在國際上有一定的亮眼成績,蘇逸華解釋:「並不是說這些片子較差,也不是獨創性不夠,應該說這些片沒有所謂的國新「體質」,但我們還是會把值得觀察的導演放來這個單元介紹,也是不想被侷限,希望影迷們注意到。」
至於「體質」是什麼?謝璇以張國榮為例解釋:「張國榮有所謂的『巨星相』,而長得跟張國榮一樣帥的是不是很多?和他一樣有才華的人是不是也很多?但那些人都沒有『巨星相』,為什麼?沒有人知道。入選國新的片子也就是一種感覺吧,有些片子就是有『國新相』,有些則沒有。」

蘇逸華則補充:「『未來之光』單元中,其實有很多部片子都在國新討論名單,或許是故事比較貼近觀眾,也或許是敘事相對來說沒那麼新穎,我們還是覺得很好看,但國新就是一個氛圍。像是《人工失格》,我們是放進『當代精選』單元,《人工失格》我們選片小組都很喜歡,雖然是導演第二部劇情長片,卻非常成熟,完全沒有新的氣息,我們便認為不用放入國新,這部片有自己的光芒,我們是希望藉由競賽平台將一些相對來說比較難受矚目的片子讓更多人知道。」
至於提到疫情的影響,蘇逸華坦言看到報名數字下降到412部時也有嚇到,推測是疫情阻礙國際影視製作上的速度,至於在實體拷貝帶的運送部分,也因國際物流受到阻礙進而推遲,但改以線上傳檔案的方式解決,不過國際影人無法來台的損失卻很難彌補,畢竟入選國新的劇組,往年慣例都要到現場與影迷互動、交流,也是國新一大賣點。
非常時期有非常做法,蘇逸華說:「我們與接待組、媒宣組跨組討論,應變之道是我們克服時差,利用線上的方式和這10部劇組代表各進行30分鐘的問答訪談(台灣的就會到現場),我們很高興創作者們都願意配合,這樣可以拉近創作者、作品和觀眾的距離。每部作品第一場放映完成後,各影片的影人訪談就會放在YouTube。」

謝璇則說道:「我不相信這樣做能取代現場問答,主要是觀眾看完片子後可能會有問題和好奇,由創作者親自解釋是非常好的過程,但這的確是在特別年度的應變方式,希望能盡量完成我們要做的事。而今年在做線上訪談的時候,發現創作者都很積極參與,感受到他們的心意,很受感動。有趣的是,他們會說想來台灣。也稱讚我們防疫成功,羨慕還能辦影展。」
謝璇持續補充:「今年也沒有頒獎典禮,目前的做法可能是先通知入選的片子決定得獎名單的時程,再看得獎者能不能給予回饋,再做後續處理。」於艱困中求變,利用線上的便捷稍微彌補現實中的遺憾,是今年國新給出影迷的答案。
新銳導演的魅力,某程度在於永遠不知道會端出什麼菜色,上一幀畫面或許會有神來一筆,令人為之驚嘆的調度,下一秒卻可能因為某種瑕疵毀掉全片,看新導演的作品就像是《阿甘正傳》那句名言:「永遠不知道嚐到哪種口味。」看國新多年,每年也總是在這單元找到驚喜,三年前專訪新加坡導演陳敬音(以《親愛的大笨象》入選國新),陳敬音應答的談吐,自信中帶著點初試啼聲的小心翼翼,與影像不謀而合,也正是這種氣質與未知,讓影迷能恣意徜徉於影像的生命力當中,不帶偏見與成見,純粹享受不同可能性,台北電影節的國際新導演競賽,也正逐漸成為挖掘新的電影語言的另一種殿堂。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
TNL 網路沙龍守則
TNL網路沙龍是關鍵評論網讓讀者能針對文章表達自身觀點的留言區。我們希望在這裡,大家可以理性的發表自己的看法,並對不同的論點保持開放心態,促進多元意見的交流與碰撞。
現在網路上的留言討論常淪為謾罵與攻擊的場域,反而造成了彼此更大的歧異,無法達成討論與溝通的目的。
為了改善這個問題,我們希望打造一個讓大家安心發表言論、交流想法的環境,讓網路上的理性討論成為可能,藉由觀點的激盪碰撞,更加理解彼此的想法,同時也創造更有價值的公共討論,所以我們推出TNL網路沙龍這項服務。
我們希望參與討論的你謹記以下幾個基本守則,與關鍵評論網一起提升網路沙龍的品質:
- 尊重多元:分享多元觀點是關鍵評論網的初衷,沙龍鼓勵自由發言、發表合情合理的論點,也歡迎所有建議與指教。我們相信所有交流與對話,都是建立於尊重多元聲音的基礎之上,應以理性言論詳細闡述自己的想法,並對於相左的意見持友善態度,共同促進沙龍的良性互動。
- 謹慎發言:在TNL網路沙龍,除了言論自由之外,我們期待你對自己的所有發言抱持負責任的態度。在發表觀點或評論時,能夠盡量跟基於相關的資料來源,查證後再發言,善用網路的力量,創造高品質的討論環境。並且避免對於不同意見的攻擊、惡意謾罵言論。
為了鼓勵多元評論與觀點的碰撞激盪,並符合上述兩個守則前提下,我們要求所有沙龍參與者都遵守以下規範,當您按下同意開始使用本沙龍服務時,視為同意此規範:
- 您同意為您自身言論負完全法律責任,您不會發表不適當言論,包含但不限於惡意攻擊言論、歧視言論、誹謗言論、侵害他人權利或任何違法情事。
- 您同意您不會張貼任何帶有商業行銷或廣告直銷之勸誘式廣告內容。
- 本集團有權管理沙龍所有內容,以利維護沙龍良性的溝通環境與氛圍。
- 本集團有權隨時新增或修改此規範,如有增修將公告於本網站。若公告後您仍繼續使用本網站,即視為同意接受增修版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