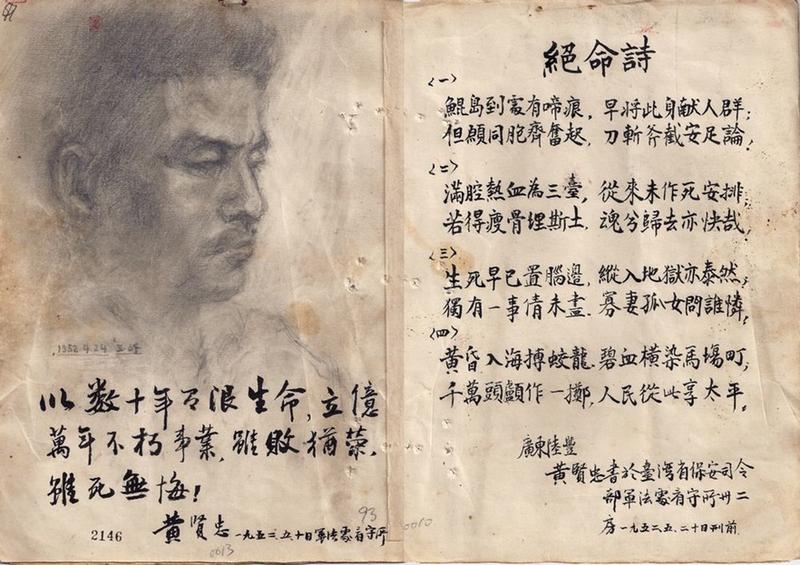我是感覺死的人已經死了,活下來的人真痛苦。咱們若向別人講自己的情形,大家也很同情咱們,但是對方能夠感受到的,只是皮毛而已,而我們自己的感受是沒有辦法可以形容的。有時候連煩惱和哭的時間也無,後面有那麼多的人要吃,民生問題要解決,就像有人講,無閒到連破病的時間也無。 我若心情無好,阮以前那個先生就會出現,我會夢到伊,伊都靜靜地在那裏,無講話,我會問伊:「你去那裏?為什麼無回來。」沈秀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頁94。
20幾個人成馬蹄形圍坐,林黎彩憑著感覺,從中挑出身材微胖的學員,代表她的父親,另一位瘦高的女性,代表母親。不久,他們倒在地上。
死去的父母像是活了過來,又死了一次。
1947年228動亂漫延到高雄,時任苓雅區區長以及新生報印刷廠廠長的林界,在3月6日隨地方仕紳赴壽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與司令彭孟緝談判,數天後被槍殺處決,那時林黎彩僅14月大;8年後,小學三年級的一個平常下午,她最後一次摸著冰涼的母親,倒在廚房門口邊,喝下的濃鹽酸使脖子到胸膛一片黑。
父母雙亡後,林黎彩與姊姊寄人籬下,在親戚的歧視目光與言語傷害中長大,並度過一段在外流浪的歲月,因為恐懼再次受到傷害,婚後封閉起自我,連左右鄰舍都不敢往來。直到解嚴初期,在夫婿廖中山(1934-1999)的支持下,一步步挖掘父親身世,並積極參與受難者家屬的倡議行動、舉辦以228為主題的美術展,更實際付諸行動向「加害者」討公道:1992年控告彭孟緝殺人罪、2010年控告國民黨,並多次於公開場合向時任總統馬英九嗆聲。直到現在,每年228仍能見到她在公開場合控訴「元兇」蔣介石的不義。
「根本想不到那個時候會冒出很多很多根本講不出來的話,我跪在地上開始怨嘆父母,抱怨小時候受的傷,你們會生不會養⋯⋯」林黎彩回想起2006年女兒替她報名參加的「家族系統排列工作坊」,在代表父母的學員前,瞬間潰堤,回到那個渴望父母擁抱的小女孩,與長年以來堅毅、強悍的公共形象形成劇烈的反差。
此輔導技巧源自德國心理治療大師海寧格(Bert Hellinger),發現許多心身問題或困擾都是源自潛意識上與家族成員的糾葛牽絆,透過「排列師」引導,一步步將問題的根源顯露,便能找出化解的方法。
「有陣子在國外念書,每年228打開電視,固定會在華語頻道看到我媽,想家的時候,這是唯一可以看到她的機會。」廖啟凡說起留學時,與母親林黎彩的隔海相望,弔詭的是,這卻是她極力想要抗拒的「紀念日」,「就像祖宗牌位,每年到這個時間點拿出來拜拜,然後再收回倉庫。這麼久以來,一方大聲疾呼追求真相,另一方則說不要撕裂族群,完全沒有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對我來講沒有什麼意義。」
與之保持距離,更深層的原因出於自我保護。不同於學者、政客、憤青等為了不同目的,紀念、研究、消費這個巨大的象徵,對受難者後代而言,228不是一個議題,而是永遠存在生命旁側,得與之搏鬥的陰影。
「我媽他們受過比較嚴重創傷的這一輩,有個通病,很喜歡栩栩如生地描述一些很可怕的畫面,讓我可以非常清晰地想像,就好像站在旁邊看那過程,比如人被用鐵絲串起、外婆自殺時的情景⋯⋯可能是因為那些東西過於強大,我想要逃,也有可能身為老么愛自由,得想辦法讓自己繼續往前走,脫離那些包袱,過好自己的生活。」
義憤的母親直面歷史的暴政,索求正義;女兒背轉身,尋找個人的出口。兩代看似無交集的道路,卻偶然的交會 。
「剛開始因為想處理個人感情的問題,接觸一些心靈治療與成長的課程,我也想要我媽去上,可是她都不肯,彼此的關係很緊張,覺得為什麼都不願改變?後來我發現到,她從小坎坷的這樣過來,生命裡面很大的重心,就是對國民黨的恨,一但把這個『恨』抽走,生命的重心就會沒有。」廖啟凡說。
某次家族排列課程後,在沒有透露任何細節的情況下,代表廖啟凡外婆的同學過來說,「啟凡,好奇怪,剛剛我覺得喉嚨好痛」,使她非常訝異,下定決心一定讓母親參加,沒有事先知會,就花了6,000元幫她報名兩天的工作坊。
「我們母女在那一段時間講沒兩句話就僵住,我講她不接受,她講我我也不接受,」起初林黎彩十分看不慣女兒花費大把金錢、時間與精力,從早到晚投入那些可疑的課程,甚至還直接進入課程顧問公司工作,「問她到底在哪裡上班,她說要保密,哪有這種事?至少要跟妳媽講一下,這樣子到底是幹什麼!薪水那麼低時間那麼長,從早上出門到半夜一兩點才回來,長期這樣對身體不行,我說老闆在利用她的善良,因為看到媽媽的痛苦,想要化解同樣心裡有傷的人。」
當林黎彩半信半疑去了女兒推薦報名的課程,相同的情境重現,代表她母親的學員,出現喉嚨疼痛的反應,彷彿多年來在外奔忙,以層層堡壘護衛的傷痕,以另一種形式,在他人的感知中坦露出來。
「兩天的課程結束,大概有半年時間,我每天早上起來,直接在心裡跟父母請安,剛開始也是一直在抱怨,到後來,還是感恩吶,沒有你們,也沒有我。雖然心裡的傷痛無法一下子好,但是最起碼,我已經往前踏出一小步。」
在這個與逝去親人連結的時刻,國族、正義、真相、責任,所有關於政治正確/不正確的名詞與概念,似乎都很遙遠。
「當我去做心靈治療課程的時候,就會想到228的家屬,許多情緒暴躁、易怒、多疑,每一個受傷的心靈,都留下難以回復的傷痕,這個社會必須要有能夠療傷的空間。」林黎彩說。
解嚴前夕首次由民間發起的平反運動距今已30年,228早非禁忌,從訂定紀念日、金錢賠償到兩度國家級的調查報告,政府從公共的層面,試圖處理、彌合這道台灣歷史上的傷口。只是公共的轉型與和解,真的能夠撫慰個人創傷嗎?這個社會能有療傷的空間嗎?
當主流的228論述核心,仍聚焦在許許多多殞落的台灣菁英,遇難的細節被不斷復述,他們過去的生命凝結在時空中恍若永恆,被留在世上的家屬則成為法定代理人,向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申請補償金,需要重構歷史情境時,則成為受難者的生命代言人。
「那些在恐怖中艱苦扶孤,活下來的女人的聲音不見了,或是我們若聽到他們的聲音,也是因為我們要他們告訴我們,他們丈夫當年受難的情形,這些女人自事件後,艱苦尋求出路的故事,只是零星的點綴在他們男人的故事後,而不見其主體性。」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沈秀華在1997年出版的《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中寫道。
1990年代初期,當她首次在宜蘭地區進行228口述史工作時,「很疑惑為什麼死的都是男人,女人的經驗到底怎麼一回事?」由此問題意識出發,在那個家屬猶仍驚懼不願錄音,並時而要求匿名的情況下,沈秀華用手寫記下在228事件中失去丈夫的女性,長久以來不被看見的生命史。
「從性別分工的角度,公共事務以男性為主,國家暴力往往針對那些威脅到權力的男性,而當男人死了、被抓去關,承受苦難、收拾接下來局面的卻是女性。當我們紀念、歌頌男性受難者,將他們寫進台灣歷史的主體,卻沒有看到那些家屬在後面,非常幽微的生存狀態。」沈秀華說。
「受害者仍定位在當時死去或被關的人,他們的父母、配偶、小孩只被當作『家屬』看待,以代理人的身份,領錢、參加紀念活動後,彷彿創傷到此結束。可是這樣是行不通的,儘管我們再怎麼紀念,他們都不會覺得『正義』真正到來,當年所留下各種的驚恐與痛苦,那些東西絕對不是我們有權力叫他放下就能放下的。」她強調。
近年來在「轉型正義」大旗下,面對國家侵害人權的過往歷史,又有新一波包括從司法正義、檔案真相、歷史責任等面向的議論與探索,只是在論述的洪流中,深深烙印在家庭中的受創經驗,繼續被遮蔽在歷史與政治的舞台之後,沖散四溢,彷彿那注定是各自要去承受並設法解決的個人逆境。
當長年站在第一線的228家屬林黎彩在坊間的心理課程中, 隨著「排列師」的引導一步步放下對過早離世父母的埋怨與羈絆時,她所背負的一切,與旁邊學員從失婚到喪子的各種創傷並無太大不同,具體而微反映出,政治暴力在家屬身上所留下的創傷經驗,是如何徹底地在政治暴力的歷史中缺席,以至於「去政治化」。
30年來,這座島嶼不斷地紀念228,但從國家體制到心理與精神醫療專業,對於正視此一創傷經驗的存在及其影響,仍有大片空白,遑論療癒的可能。
「雖然那是國家應該做的事,但年復一年的紀念儀式我其實蠻無感的,覺得好遙遠。坦白說當初進來這裡工作,想要探索那個黑暗的歷史,彌補自己心裡的黑洞,可是我找不到,因為都是英雄豪傑、台灣菁英,那我的母親呢?我的哥哥呢?被糾結得這麼深,誰描述過他們、誰注意過他們?」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研究專員林小雲坦言,她的父親林傑鋼於1950年白色恐怖時期被捕,判刑15年送往綠島,出獄後生下她。

「在這個紀念館,常常政治直接就打過來了,被卡住、肢解,完全碰觸不到真正的生命,個體被模糊在一片大論述之中。」她表示。
與228類似,過往對於白色恐怖議題的關注多集中在受難者的遭遇,紀錄工作與詮釋角度則多由學者以及文史工作者掌握,2014年,幾位戒嚴時期父親涉及政治案件的「二代女兒」,在藝術家蔡海如的策展下,以藝術創作的形式傳達女性家屬的經驗,如此家屬自主的發聲可謂空前。
「這個展覽好像一種儀式,跟悶起來私下聊不一樣,我們鬱積這麼久,不知如何解決、搞不清楚的狀態,突然好像有了一個不一樣的出口。」林小雲說,她是當時的參與者之一。
相較於228,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其家屬的經驗,更難對大眾敘述並被理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許多案件牽涉到左翼共黨組織,尤以1950年代居多。對於從戰後歷史建構民族認同的後解嚴世代,摻雜在白色恐怖時期中的「政治不正確」成分,使其難以進入台灣國族敘事的殿堂。
沈默與壓抑,則普遍籠罩在每一個「白色家庭」內部。
「他們可以對朋友講這段重要的經歷,可是對子女一字不提,也不能問,從小母親就很在意我怎麼跟別人介紹自己,叮嚀不要講父母名字、非必要不要告訴別人家住址,所以若要我自我介紹,腦袋會空空的。」參展者之一顏司音說,父親顏大樹1950年入獄13年,出獄後才結婚生下她,「我爸1991年走,為了尋根,我的碩士論文書寫他的經歷,口試時老師問,為何沒寫『自己』的感受,我心想哪有那麼簡單?從小到大不能說,現在要說,我會失語,又要從何說起?」
在父親「被消失」以及「回來後」不順遂的歲月中,永遠是母親撐起家的重擔,與母親之間的拉扯,橫亙在女兒們最重要的成長階段。
「媽媽很兇,小時候對我來說像巫婆的角色,因為很厭惡爸爸以前的朋友,認為都是外面的社會關係,造成了他的災難,所以在我記憶中,媽媽總是很緊張告誡不可以這樣、那樣有危險,不要跟旁邊小朋友玩,家裡有種很奇怪的封閉性。好像隨時戴著一個玻璃罩,外面多熱鬧,我怎麼走,還是被封在裡面。」林小雲說。
直到展覽前夕,這些來自不同生活背景、省籍,過去大多不識的「二代女兒」,初次碰面聚會,赫然發現彼此像「孿生的靈魂」。
「那是一次很奇妙的聚會,平常我們無法開口對別人講的事情,每個人很熱絡的就談起來,並覺得天吶!為什麼這麼容易就能了解彼此,每人都講了好長好長的故事。」林小雲眼睛發亮地說起那個場景。
不在場的父親、神經質的母親、身處局外人的孤單感受,甚至是不知從何而來的身體疼痛⋯⋯已過中年的女兒們,拾起斷裂的記憶,從語言的縫隙中,傾聽、看見並描繪長久以來不足為外人道的一切。
「家屬在自我表達上是很困難的,要顧及到『英雄』的角色,這個不要寫、那個不要講,我們真正的感受是比較次要的,如果說這是一個療癒的過程,那永遠沒有辦法到盡頭,因為我們始終要隱身在那個光環底下。」施又熙也是參展者之一,原名施珮君的她,是施明德第一段婚姻的次女。
從小到大,都要被與著名的父親放在一起談論,即便幾乎沒有相處機會,甚至最後走到衝突決裂,「小時候就像穿上盔甲忍耐著,相信明天一定比今天好,因為他去坐牢所以我們才會這麼衰,可能對於父親有個渴望,一直懷抱著一點希望,等他回來就會好了,後來發現更糟,一輩子唯一仰賴的一點點東西,整個崩塌掉了。」
走過自殺邊緣與6年的憂鬱症治療之路,施又熙的作品名為「你看得見我嗎?」,在一面面鏡子上寫下文字,其中一面寫著:「那個年代,我看不見自己,現在,年近半百,才開始學習看見自己,但,我的青春人生呢?」
每一件作品訴說的,都是看見自己的渴望,還有試圖看見家人苦難的源頭,與遺憾和解。
林小雲把父親在綠島的照片,與母親獨立在山上與兄姊的家族照,在兩面相對的牆上並列,還有3幅洗不出來,「假如歷史沒有被無端扭曲,我父母可能可以擁有的比較自然而美好的生活照」。
林小雲本想將這個展覽,當作禮物送給臥病多年的母親,可是來不及能看見,她就去世了。勉力出席其中一場座談,面對張著好奇雙眼的年輕觀眾分享,當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到母親,她嚴厲的面孔從小到大都沒有出現在夢境中。
「場景在小學四年級的教室,那時剛從山上搬到城市,裡面是我們家建材行的擺設,從教室出去,在走廊盡頭遇到我媽,夢裡的她很完好、雍容,身上穿著熟悉的花襯衫與黑長褲,用母語饒平腔客語對我說:『毋思忒煞猛』,意思是『不用那麼拼命』。笑咪咪的神情,意味著她知曉也感受了我的努力,要我放鬆些。」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